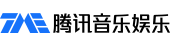简介
这首歌编曲上的纯粹性也是创作者力图做好,并拒绝与过去重复的一个向度。爱尔兰哨笛,吉他皆由彝族音乐圈内顶尖的音乐人参与实录。配器编排总体上是及其简约的风格,和声除了老鹰自己和说果九古外,也只有勒者阿则唱的干干净净的几句女声。 彝语歌曲《忧伤的歌》中所描述的是一个历史的横切面,这样的歌说白了不是为流行或者商业刻意准备的。它的格局有一种掷地有声的品格,那便是在扣问族群的历史尊严,转型期社会伦理异变的纬度,以及传统智慧资源遭遇现代性时表现出的表层的贫乏幻象,与当下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。 歌曲词句里对位的冲突张力,直面了当代彝人社会生活的破败之面,几乎是提前进入了母语重度缺失,民俗全面变异的“后彝人”时代。你说杞人忧天也罢,庸人自扰亦可,但历史的断裂早已蓄谋已久,而有的不甘心的创作者就是不愿随波逐流,敢为人先,撕开这份众所周知而依旧伪装着的假面。在我看来,这就是商业艺人与纯粹艺术家的本质区别。不妥协的感性也许处处都要遭遇难题,举步维艰,但它的纯粹兴许也是最易让时代记住的,让历史无法逃避的。而不失格的理性处理,可能就是一种如虎添翼的突围,资本时代的资本善用也是艺术创作服务灵魂救赎的重要供给策略。 在当下的传播与接受机制下,一首诗歌,一部小说,也许都不及一首歌曲更为直接简洁的深入人心,而我们要如何去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完成很好的和解,可能就是歌曲之外的事情了。它的主要功能是点开我们所处的“病态”,让我们不至于彻底绝望,而满怀希望的去直面我们的“病态”。 去掉一种语言即是在去掉一种人类的文明书写,它实则是在毁灭整个人类的丰富性与创造性。现代科技的发展,人工智能的突破,如果仅仅是为了沟通需求,是不再有必要强制学习任何一种语言的。母语是一个族群的文化书写叙述命脉,它一旦死亡,这一共同体构建的文明大致也就只能在博物馆静候猎奇的眼神了。而完全丧失母语,丧失文化的一代人可能也不存在血脉意义上的共同体了,那样一种状态即是族群的彻底消亡。至于在身份证上印了什么群体,那都无济于事,当然也就无所谓了。把“自我”送进坟墓的一代少年或者精英,就是对阉割始终报以奴性幻想的一代。吉克曲布这首《忧伤的歌》针砭时弊,一针见血。在我看来,我们这个时代的挽歌已然写好,它便是《忧伤的歌》。创作者都不忍心直白的将那种来自生命底部的绝望挑明,而是报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在加持着希望或者涅槃重生的美好。有效的传统的尊严,族群存在之生命品格,在歌中被召唤,被挽留,被无数次地轮回重构。